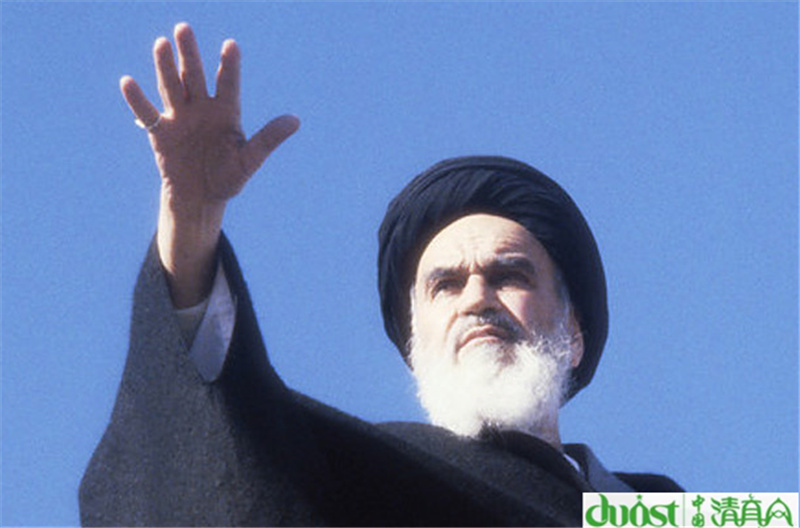清真寺文化淺論
清真寺,伊斯蘭教建筑群體的型制之一,是穆斯林舉行禮拜、舉行宗教功課、舉辦宗教教育和宣教等活動的中心場所,是阿拉伯語“麥斯吉德”的意譯。“清真”一詞,在漢語中原作純潔質樸解。明清之際的中國回族學者在解釋教義時說,“清”是指真主清凈無染。不拘方位、無所始終;“真”是指真主獨一至尊、永恒常存、無所比擬;“寺”則是沿用了中國古人對佛教、景教、襖教等宗教的宗教活動場所的稱謂。由此可見,“清真寺”的含義要更深遠、更含蓄,涉及的范圍也更廣泛,可以說,“清真寺”已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稱謂了。
隨著中國伊斯蘭教的傳播和發展,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清真寺文化。清真寺已不僅僅是傳統意義上的宗教活動場所,而具有了獨特的社會功能和復雜的文化特色,它既是穆斯林社會政治活動的中心,一個相對獨立的經濟實體,同時還是穆斯林的文化活動中心,一個重要的教育機構,它具有一種行為規范和社會控制功能。清真寺的這些功能共同構成了獨特的中國清真寺文化。
中國的清真寺文化涵蓋面很廣,清真寺的最根本的職能是舉行宗教活動,而宗教活動是一個群眾性的活動,“人”在其中具有很大的影響,所以就逐步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宗教組織制度,即教制文化;清真寺作為伊斯蘭文化的一種有形載體,它對穆斯林物質生活和精神文明有著重要的影響,它是伊斯蘭文化的最主要的研究、傳播地點,在伊斯蘭文化的研究和發揚過程中,教育是成為不可缺少的因素,隨著歷史的演變,形成了中國的清真寺教育文化;清真寺作為一個宗教活動場所,有其具體的建筑型制,所以有其建筑文化。教制文化、教育文化和建筑文化是中國清真寺的主要內容,是中國清真寺文化的精髓,對這三方面的分析與研究是對了解中國清真寺,發揮清真寺重要社會職能有著極其深刻的意義。
教制文化
教制文化具體體現為教坊制度。教坊是中國伊斯蘭教的傳統組織形式之一,它是以清真寺為中心,包括周圍穆斯林居民的一種宗教和社會的群體單位,它具有二個明顯的特點,第一是獨立性:凡是十幾戶、幾十戶、幾百戶,無論人多還是人少,還是穆斯林聚集地區,一般都有一座清真寺,聘請一位阿訇任教長,領導一坊過宗教生活,凡在該寺舉行宗教活動的教民,都屬于該寺的坊民,歸教長負責,對本寺盡義務。這一區域便形成一個以清真寺為中心的教坊,與其他教坊無任何隸屬關系;第二,教長聘任制:各坊的教長,由本坊教民在德村兼備、德高望重的阿訇中擇聘,教長既非世襲,也無特權,即可是本坊人,也可是外坊人,但因親戚家族等緣故,為便于宣教,一般都不請本坊阿匐。教長任期三至五年不等,可以連任。
教坊的地域性和獨立性導致清真寺有一整套組織機構,其經費來源主要來自本坊教民的乜貼,但隨著改革開放,現在不少清真寺實行了“以寺養寺”,有了清真寺的企業,其經費也不再單純依靠教民捐助。
清真寺內的組織是逐步完善的,唐宋時有管理教務的“篩海”教長和管理民事的“嘎錐”(宗教法官),后來形成“三掌教制”,即(一)伊瑪目:又稱“掌教”,專司領拜和掌管教規八二)海推布:又稱“二掌教”或“協教”,專門負責宣讀“呼圖白”,通過誦經說教來勸導坊民。在河北、山東、東北一帶,海推布為認行洗禮;(三)穆安津:亦稱“三掌教”或“贊禮”,是清真寺的宣禮員,每天按時念“邦克”,召集大家來禮拜。在三掌教之外還設阿訇一職,阿訇不同于三掌教的世襲制,而實行聘任制,阿訇作為教長,教職最高,受聘于一坊,主持該坊的全面宗教事務,擔任開學講經及宗教學說的教授工作,故又稱“開學阿訇”,此外,阿訇還為教民舉行各種宗教儀式。伊斯蘭教最初傳人中國,既無派別,又無門宦,統統是相習傳教,后被稱為“格底術”(老教)。三掌教制是“格底木”的教坊制度。在明末清初,蘇非派(神秘主義)傳人中國,后來形成門宦,門宦教主對其所屬教坊,實行嚴格控制,于是產生了“熱依斯”制和“穆勒什德”制。他們都代教主管理一個區域內的數十個教坊,有的“熱依斯”后來獨挑大旗,成為獨立的一支派,有的代代相傳,成為世襲制。
十九世紀依赫瓦尼傳播后,“海乙寺”制又相繼出現,“海乙”是阿拉伯語語的音譯,其意思是“地區聚集地”、“海乙寺”與一般清真寺就像鄉鎮與村莊的關系。一個海乙寺,管轄十幾個或幾十個小寺。海乙寺的掌教管理所屬小寺的阿匐,有出“候昆”教法和處理民事糾紛的權力。
“三掌教”制、“熱依斯”制和“穆勒什德”制及“海乙寺”制,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都有不同程度的改變,但它在中國伊斯蘭教史上的作用是巨大的、是不可磨滅的,教坊制度為有共同地域、共同語言和共同心理特征的回回民族的產生起到了紐帶的作用,有其重要的歷史意義。
當今中國清真寺的組織機構,大多是由民主管理委員會處理事務,聘請阿訇處理教務,三掌教制已發生了質的變化。中國清真寺的教坊制度也在隨著社會的發展不斷地改變和完善。
教育文化
在伊斯蘭教史上,教育一開始就與清真寺結下了不解之緣。誦讀《古蘭經》,學習《圣訓》是穆斯林教育的首要內容,而這些活動都是在清真寺進行的。因而清真寺便成了穆斯林教育的搖藍。教育對于中國處于亞文化地位的伊斯蘭文化尤為重要,而清真寺在其中則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中國伊斯蘭教的教育始終沒有脫離開清真寺。中國伊斯蘭教育的主要形式回回經堂教育便是誕生在清真寺,它在傳播伊斯蘭教、弘揚伊斯蘭文化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貢獻。經堂教育又被中國伊斯蘭史學家稱為寺院教育,便是清真寺所在經堂教育中的地位的具體體現。所以,可以把中國清真寺的教育文化具體為經堂教育制度。
“經堂”本是我國清真寺中建筑布局的一個場所,清真寺是主體建筑回回禮拜殿南北兩側均有對稱的廂房,而阿訇講經的廂房便被稱為“經堂”,“經堂教育”由此而得名。經堂教育是公元七世紀以來,隨著伊斯蘭教傳人中國而逐步發展起來的,經唐、宋、元、明四個朝代的漫長歷史歲月,到明末已初具規模,經堂教育的集大成者回回胡登洲便生活在這個年代。
胡登洲(1522年――1597年),是長安城北渭城灣人氏;家道小康,自幼刻苦攻讀宗教經書,并兼習儒學,胡登洲多年蓄志,謀求中阿波譯述融匯貫通,并制定出一套經堂教育大綱。他刻苦鉆研、孜孜不倦,在其五旬之際,終成宏愿,他在家自辦教館,收徒百余人。他的這一舉動影響很大,在他的精心培養和教育下,人才輩出,桃李滿天下,從而為中國經堂教育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經堂教育的宗旨和形式
經堂教育的創立,旨在改變回回民族愚昧無知的狀態,提高穆斯林的素質。《經學系傳譜》明確指出:“人皆知以食愈饑,莫知以學愈愚。人之饑猶可也,愚則必不可也。只緣愚則必惑,終至于迷耳。”胡太師卓識遠見,深刻理解文化知識對于人們立身處世的迫切需要。所以五十而立仍學習詩書,繼而皓首窮經。最后創辦經學,其宗旨就在于通過教育手段,提示伊斯蘭教理,教育穆斯林道行經訓,培養穆斯林宗教人材。
經堂教育的形式,一般分為大學、中學、小學。趙振武在《三十年來中國回教文化概論》一文中介紹說:“所謂寺的教育者有大學、造就阿訇之學府也;有中學,中年失學者受教處也;有小學,兒童之教育也。”經堂小學主要是向穆斯林兒童和少年進行伊斯蘭教知識的啟蒙教育,讓他們通過學習,掌握伊斯蘭教的一些基本知識,學會一些《古蘭經》中部分常用的章節。中學教育的對象是從小沒有受到系統教育的成年人,學習的主要內容是《亥貼》。大學里主要培養專門的宗教人材,畢業以后多被聘去講經或任開學阿匐。大學學制無定制,以學成為準由此可知,經堂教育的使命主要有兩個:一是在穆斯林青少年和成年人中普及宗教知識,二是培養未來的伊瑪目,伊瑪目的職責是弘揚教義、教法,主持宗教活動和婚喪禮儀,處理穆斯林內部的民事糾紛。經堂教育的課本及課程概括地說,經堂教育的全部課程分為基礎課和專業課兩部分。基礎課包括語法學、修辭學、邏輯學。實際這些都是掌握阿拉伯語的工具課。專業課包括:認主學、教法學、圣訓學、哲學、《古蘭經》注及波斯語文法等。
一般而言,經堂教育的大學課本中有十三讀本,是各地經堂教學中必讀的。俗稱“十三本經”。分別為:
1、《連五本》;2、《遭五.米素巴哈》;3、《滿倆》;4、《白亞尼》:5、《凱倆日》;6、《韋噶業》;7、《呼托布》;8、《古力斯坦》;9、《艾爾白歐》;10、《米爾薩德》;11、《艾篩爾圖.來麥爾特》;12、《亥瓦伊.米那哈基》;13、《古蘭經》經注。
經堂教育的課程體系形成于經堂教育的后期。在陜西,經堂課程設阿語語法學、修辭學、邏輯學、教法學、理學、認主學。前三門屬語言課程,后三門屬宗教課程。
至于經文小學,并無沿革的課程設置。
胡登洲創立經堂教育之后,培養了大批經師,他的弟子和再傳弟子們將經堂教育制度進一步加以發展完善,到了清朝,他的再傳弟子們活躍于東西南北各地,并逐步形成具有地方特點的不同學派,其中最具特點的是;
1.陜西派,也稱“陜學”,以陜西為中心而著稱。系胡登洲倡興,中經馮、海二先生,蘭州馬、擺阿匐等幾代至周老爺時發揚光大而奠定了堅實基礎的一個經學學派。其經學風格是阿拉伯語和認主學的課程。講授方法精而專,往往一位阿匐只專一門。有以二十年功夫講授一本經典的,經堂學生如欲兼學另一部經典,則需另投一位經師。西北、河南、安徽多屬此派。
2.山東派,中心在山東省濟寧。系由胡登洲的四傳弟子常志美、李延齡倡導的一個經學學派,其經學風格是博而熟。即阿拉伯語、波斯語兼學并重。
此外,還有云南派等。
早期經堂教育突出成就是:人材輩出,群星燦爛。在《經學系傳譜》一書中趙燦評價“吾清定鼎以來,學者之多,人才之盛,宛如列星。”最具代表性的經師有:
胡登洲,經堂教育的倡導者,被尊稱“大師”。
常志美,字蘊華,11歲進寺學習阿拉伯語、波斯語和伊斯蘭教經典。學成后在濟寧設帳于順河清真寺。為經堂教育山東派的形成打下了堅實基礎。
馬聯元,云南新興人,經學世家。幼隨父念經,兼學國文。后隨舅父赴麥加。并游學土耳其、伊拉克,學習《古蘭經》讀法等課程。回國后廣招生徒,提倡中阿并授。經堂教育的歷史階段
(一)形成階段
明朝中葉,胡登洲首先在陜西西安開始招收若干弟子于家中,傳授伊斯蘭教知識,后移至清真寺辦學。這時只是經營教育的初期和雛型,仍沒有大規模地形成一種制度。
經堂教育首先在陜西興起,這絕非偶然。陜西是古代中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西安是絲綢之路的起點,為十四朝古都。同時,這里是伊斯蘭教傳人最早的地方。也是穆斯林聚居的主要地區之一。陜西為中國伊斯蘭教文化的發源地,也是中國伊斯蘭教發展最快、最興盛的地區。
(二)發展階段
在胡登洲的培養和教育下,他的學生桃李滿天。人才輩出,紛紛設帳講學。從而為中國實施經堂教育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使經堂教育逐漸發展成一種伊斯蘭教育制度。此階段寺院經堂教育已遍布全國不少地方。在山東、云南、東南沿海等地也有較大規模的經堂教育。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陜西派、山東派、云南派等。出現了象馮先生、海先生、常志美等一大批著名經師。
(三)繁榮階段
這個時期的經堂教育,各地已逐步形成各自的中心,最具代表性的是云南派和金陵派中劉智、馬注等人,翻譯了大量典籍和經堂教材。
在云南,以馬復初、馬聯元為代表的云南派,他們從國外游學而歸,設帳開學,著書譯作,翻譯題材涉及廣泛。由宗教哲學、宗教典制擴大到天文歷法、地理等方面。并開始《古蘭經》的漢譯。馬復初所譯《寶命真經直解》是中國首部漢澤《古蘭經》。
正如著名學者張秉擇說:“也正是在這種教育制度下,造就了一批批著名伊斯蘭學者……這也是經堂教育的成果之一。”經堂教育的特點和歷史貢獻
經堂教育的特點
中國伊期蘭經堂教育歷盡滄桑,對中國伊斯蘭教的傳播與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貢獻。直到今天還有著巨大的生命力。這是因為經堂教育不僅具有正確的辦學方針,同時,是因為中國經堂教育長期摸索和積累了豐富的教學經驗,形成了優良的傳統特色:
一、搬請開學阿訇制度
經堂教育實行聘任制,能開學教學的清真寺都需聘任開學阿匐。經堂教育選拔師資十分嚴格。做為經師除了“傳道授業”外,還必須具有高尚情操,在穆斯林中起表率作用。
二、口傳心授 教學嚴謹
這是傳統的經堂教育的一個特點,首先教學采用單一逐人式,實行以學科為單位,因材施教,不強調統一,不分年齡長幼,經堂教育的教學循序漸進,分初、中、高三個階段。初級教育以精通阿拉伯語語法做為主修課,接著再讀阿語修辭學;中級階段首先學伊斯蘭教信仰學綱要,接著學習教法學,這樣大約經過5―7年,學生可逐步擔任伊瑪目率領大眾禮拜;高級階段課程主要是學習《古蘭經》注釋及《凱倆目》。
三、學規嚴厲 勤奮攻讀
經堂一般對經生有一定的規章和學規。對經生的學習、生活、作風都有嚴格要求,經堂學生多不計環境優劣,一心只埋頭于學業,天天都在學習。晨禮后由阿匐講經,晌禮后學生向老師復述當天的新課,昏禮后至霄禮為復習時間,霄禮后要學習至深夜。
四、經堂語和小兒錦
經堂語是用于經堂解釋經典的一種語辭。它是經師在經堂教學中專為清真寺哈里發編制的一種翻譯方法。它是漢語式的宗教語文。它是由夾雜有大量阿拉伯語詞而以漢語表現出來的不同于一般漢語的宗教專用語。它的主要特點就是適應于口頭講授,對于每一種語法關系都有相應的口氣,能準確無誤地掌握原著的字、詞的意義和語法結構,使翻譯出的每一個詞,每一個字都那么準確,達意,緊緊相扣。
小兒錦是對通用漢語而不識漢文的阿訇、經生用漢語拼音,并包涵著阿拉伯語、波斯語的詞匯而加以拼寫的拼音文字,小兒錦是伴隨著經堂語教學相繼出現的產物。經堂教育的歷史貢獻經堂教育是在一種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特定的文化背景中產生的特殊教育形式。它的意義和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具體表現在:
一、經堂教育為在中國宣傳和弘揚伊斯蘭文化做出重要貢獻。
眾所周知,中國是一個儒家文化占主導地位、推崇佛教和道教的國家。明清統治者實行“儒釋道三教并重”的政策,把伊斯蘭教視為“旁門左道”而加以排斥和抑制。同時,還在回族地區設義學,強迫穆斯林讀儒家經典,接受儒家思想,其結果出現了“經文匿乏,學人寥落”的狀況。伊斯蘭文化面臨幾近斷裂的危機。在這種情況下,正是經堂教育,通過對教義學、認主學、教法學、經注學、圣訓學和有關的語言學、語法學、邏輯學等系統講授,使一代又一代的穆斯林重新確立了一種與眾不同的宇宙觀、人生觀和價值觀。從而使伊斯蘭文化得以在一個儒教文化占主導地位的國度里,代代相傳、聲聲不息,經久不衰。與此同時,包含著獨特的風俗習慣、文學藝術、語言文字、倫理道德、價值觀念、經濟制度的伊斯蘭文化,從另一個側面充實和豐富了中華文化的內涵,使中華文化稱謂各民族共同擁有的一種更加博大精深的文化體系
二、經堂教育的倡興,培養和造就了一大批著名經師、伊斯蘭學者、政治家和社會活動家。
經堂教育為中國伊斯蘭教培養了成千上萬的阿匐、經師和學者。造就了一代又一代德才兼備的穆斯林。許多經堂教育培養的人才成為回族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如王岱輿、劉智。馬注、馬德新、張中等都是儒釋道伊四教兼通、學貫中西、博通古今的學者。他們還以“以儒詮經”的獨特嘗試,促進了伊期蘭文化與其他文化的交流。近代的馬明心、馬來遲、馬果園、馬啟西等一批著名阿訇,既是某一派別的宗教領袖,又是社會活動家和教育家。他們不但主持日常的宗教活動,而且還常奔走呼號,傳經布道,活躍于穆斯林社會。遇到統治者的民族壓迫和宗教歧視時往往振臂一揮,率領穆斯林群眾進行反抗,為振奮民族精神、維護民族生存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唐宋時期伊斯蘭文化在中國的東南沿海地區極為繁榮。后來由于經堂教育的薄弱和消失,伊斯蘭文化也隨著銷聲匿跡。今天,我們在那里只見一些斷壁殘垣和博物館里的文化珍品,而不見穆斯林文化活生生的載體。從中也可以反證出經堂教育的歷史作用。
三、經堂教育是中國伊斯蘭宗教教育與中國教育的結合,它促進了伊斯蘭教育的民族化。
不同國家、不同民族穆斯林的宗教教育,除了其共同特點外,還有其自己的特點,這是由多種因素決定的。如民族文化傳統,語言和環境等。中國內地穆斯林的宗教教育,在回族等民族共同體形成之前,共性的東西居多,因為那時多數經師、阿匐來自境外,他們受的教育自然是傳統的伊斯蘭教育。然而,在十四世紀回族形成之后,回族文化與伊斯蘭文化的密切相關,同時受到中國傳統文化深刻的影響。中國穆斯林的宗教教育隨之孕育而生。經堂語和“小爾錦”的作用是宗教民族化的一種具體體現。胡太師一開始就注意到了回族形成后的新變化。
胡登洲“課習儒學”使伊、儒貫通一家,以儒論經,更好地闡揚伊斯蘭教義理。實現了兩種文化的結合。十七世紀開始興起的漢文譯著活動是中國穆斯林宗教教育的繼續深人和發展。漢文譯著活動的參加者多是具體教育培養出的杰出人材,是胡登洲的再傳弟子,他們能采取“以儒詮經”的方法建立起具有民族特色的宗教哲學體系。事實證明,伊斯蘭教育的本地化是歷史發展的必由之路。
經堂教育為在中國宣傳和弘揚伊斯蘭文化作出了重要貢獻,它的倡興,培養和造就了一大批著名經師、學者、政治家和社會活動家,同時它還是中國伊斯蘭教教育與中國教育的結合,它促進了伊斯蘭教育的民族化。
經堂教育做為中國清真寺教育文化的主要形式,也受到了時代的沖擊,當今,中國清真寺教育也在逐步地發生著變化。除少數地區仍堅持經堂教育外,全國大部分地區的清真寺教育都從課本、內容、授課形式上做了大幅的調整。河南、陜西、山西以及西北地區的清真寺引進了阿拉伯國家大學的教材,并開授阿語語文等課,有的清真寺還實行了課堂制,有的清真寺還開設了電腦、英語等課,并聘請教授或留學歸國的學生任教,從根本上改變了一個師傅帶十幾個徒弟的形式,實行多師多課,逐步向正規教育靠擾。這些都是清真寺教育面臨時代的挑戰進行改革調整的嘗試。相信隨著時代的前進,清真寺的教育也會逐步趨于完善,與社會接軌,并不斷地培養伊斯蘭教人才,為伊斯蘭文化的弘揚與發展注人新的血液。
建筑文化
建筑藝術與建筑風格是一種文化內涵的外在表現形式,具有非常深刻的象征意義,它代表一種文化,中國清真寺的建筑恰恰是伊斯蘭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融合的一個見證之一。中國清真寺建筑大體可分為兩大體系:一類是以木結構為主、羽翼式造型的中國清真寺建筑,充分體現了中國的傳統建筑風格,基本上是中國特有的建筑型制;另一類清真寺建筑則更多地保留了阿拉伯的建筑形式和風格。
中國傳統建筑風格的清真寺,目前我們所見到的大多是元以后,特別是明、清以來創建或重建的。明代的清真寺,在建筑的整體布局、建筑類型、建筑裝飾、庭院處理等各方面,都已具有鮮明的中國特點。而清代則是中國伊斯蘭教建筑大發展的高峰時期,中國清真寺的特有建筑型制正是在此時完全形成的。
中國傳統建筑風格的清真寺具有以下特點:
一、布局完整。中國清真寺絕大多數采用中國傳統的四合院并且往往是一串四合院制度。其特點是沿一條中軸線有次序、有節奏地布置若干進四合院,形成一組完整的空間序列;每一進院都有自己獨具的功能要求和藝術特色,而又循序漸進、層層引深,共同表達一個完整的建筑藝術風格。
陜西西安化黨巷清真寺、北京東四清真寺、牛街禮拜寺、鄭州清真寺、安徽壽縣清真寺就是這類建筑的代表作。院落的循序漸進,使清真寺顯得深造尊嚴;建筑物的井然有序,突出了清真寺的嚴肅整齊和豐富性;整個藝術形體的重重疊落,又加強了主要建筑高大雄偉的姿態和巍峨氣勢,反映了中國傳統建筑注重總體藝術形象的特點。
二、中國化的建筑類型
內地清真寺的結構體系和建筑型制,一般都具有中國的特點,這些特點突出表現在大門、邦克樓和禮拜大殿等主要建筑上。
中國式的廟門制度、中國傳統樓閣式的邦克樓、中國大木起背式的禮拜殿、勾連搭的建筑結構等都是已經民族化的中國伊斯蘭教建筑形式。
三、中西合壁的建筑裝飾
豐富多彩的建筑裝飾,是中國清真寺建筑藝術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中國清真寺建筑的鮮明特點之一。不少清真寺都成功地將伊斯蘭裝飾風格與中國傳統建筑裝飾手法融匯貫通,把握住建筑群的色彩基調,突出伊斯蘭教的宗教內容,充分利用中國傳統裝飾手段,取得富有伊斯蘭教特點的裝飾效果。
中國很多著名的清真寺,都以其精美的彩繪藝術見長。如西安化覺巷清真寺、山西太原古寺、北京東四清真寺、牛街禮拜寺、通州清真寺等,其后宮殿乃至龕上的彩畫藝術精美絕倫,顯得極其富麗堂皇。一般而言,華北地區多用青綠彩畫,西南地區多為五彩盒裝,西北地區喜用藍綠點金。何種顏色的彩畫都源于中國傳統。而這些彩畫的共同之處又在于不同動物、人物圖文、全用花卉、幾何圖案或阿拉伯語書法為飾,這是中國伊斯蘭教建筑藝術的一個顯著特色。
四、庭園處理富有中國情趣
中國清真寺大多具有濃厚生活情趣的庭園風格,反映出中國穆斯林不避世厭俗,注重現實的生活態度。他們在寺院內遍植花草樹木,設置香爐、魚、缸、立碑懸匾、堆石疊翠。園林味十足,給人以賞心說目的感覺。
五、中國清真寺的伊斯蘭教特點。
清真寺是伊斯蘭教建筑,無論其式樣如何繁多,也無論其如何吸收大量中國傳統建筑手法,都必須嚴格遵守伊斯蘭建筑的一些原則,具備伊斯蘭建筑的某些基本特點從主要建筑設置方面,一般都有禮拜殿、邦克樓、望月樓、沐浴室、米合拉布、敏拜爾構成,方向上,大殿一律建在座西朝東方,大殿內絕對不供奉偶像,也絕不用動物圖形為飾。
以上種種伊斯蘭原則,使中國千姿百態的清真寺具有共同的特色,在中國宗教建筑之林中別具一格。
二、阿拉伯建筑風格為主的清真寺在中國,以阿拉伯建筑風格為主的清真寺也不少。這類清真寺,多分布在新疆等民族地區,內地則或是早期的某些古寺或是近年來的新建寺。
中國早期清真寺采用磚石結構,平面布置,外觀造型和細部處理上,基本都取阿拉伯式樣,是以阿拉伯建筑風格為主的建筑物,這些清真寺的建造,一方面為中國古代建筑增。添了新方式、新內容;另一方面,也為作斯蘭教建筑的中國化奠定了基礎。
近年來新建和重修的清真寺,有不少都在門樓設計上吸取了穹頂式的阿拉伯風格,如北京下坡清真寺、臨夏南關大寺等。
無論是中國傳統風格為主的清真寺,還是以阿拉伯風格為主的清真寺,都是中阿文化相互交流的產物,帶有濃厚的伊斯蘭教風格,同時也表現出鮮明的中國風格和中國氣派。中國清真寺的建筑文化是中國建筑文化的一部分,同時也是世界伊斯蘭教建筑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是伊斯蘭教文化在中國生根發芽,并與中國傳統文化相融合的產物,它代表了中國伊斯蘭教文化的一個重要特點即融匯與貫通,也是世界文化交流的一部分。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了解到中國的清真寺文化是一個涵蓋很廣的綜合體,它包含了教制文化、教育文化、建筑文化等許多方面,它充分體現了中國伊斯蘭教是伊斯蘭教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相融合的特點,它是中國伊斯蘭教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