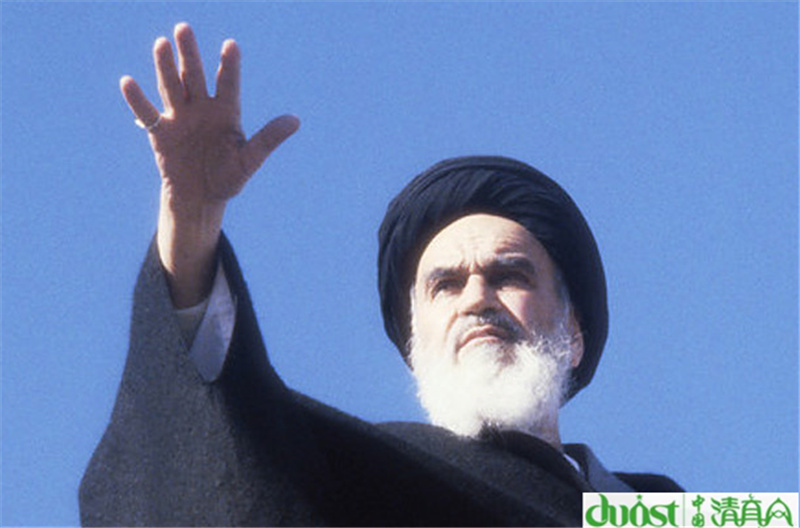丈夫為自由而亡 妻子在約旦受難
2012年,當第一批“烈士遺孀”住宅樓在約旦拉姆薩開放時,當地居民和伊斯蘭慈善機構紛紛對這些逃難的敘利亞孀婦和家屬表示接納——這些人的丈夫在抗擊阿薩德政府的過程中犧牲。敘利亞邊境附近出現了十多座這種建筑,是導致近20萬人喪生的這場沖突的一種見證。但是,這些嚴守規矩的穆斯林男子的未亡人非但沒有被當做尊貴的客人,反而日益被視作不受歡迎的負擔。幫助難民的開支正在影響敘利亞鄰國的經濟發展。而且,人們對昨日的“自由斗士”有了更復雜的看法。許多人的丈夫為之奮戰的較為激進的宗派,如今被認為可能會對約旦,以及許多支撐伊斯蘭慈善機構的海灣國家造成威脅。
圖為2012年的F,那時她丈夫還活著。她當時被她的家庭和所在社區認為是一位堅強的女人。她以前在敘利亞常坐在丈夫摩托車后座上(戴著面紗)。而當她在約旦成為難民時,她是姐妹三人中(三姐妹都是難民),唯一有勇氣穿過街道去拜訪他們的。
女攝影師Tanya經過努力取得了她們的信任,由此才得以罕見地近距離觀察這些女子——在斗膽外出時,她們會把自己完全包裹起來,只把雙眼露在外面。“她們不能離開,不能露出臉,不能暴露身體,”哈布朱卡說。“幾乎無法接近她們,從視覺角度來講述她們的故事也非常困難。我絞盡腦汁才弄明白怎樣才能讓她們覺得安全。”這些女人“非常脆弱”,她說,因為她們的丈夫為之獻身的沖突不再被人當做一場革命,而是成了一場充滿派別與宗教含義的復雜內戰。圖為88歲的M正在梳頭發,她的秀發曾經她最驕傲的東西。她正在約旦拜訪她的兒媳婦和孫子們。他們住在拉姆薩的“烈士遺孀”樓。她兒子在敘利亞戰爭中犧牲。她曾經建議她兒子在新婚之夜打他妻子一頓,以建立自己的權威。攝于2014年。
如今,因為擔心遭當地男子侵犯,除了去集市,這些孀婦很少出門。她們的女兒在10或11歲就會輟學,然后待在家里,無所事事。一名少女告訴哈布朱卡,她每天消磨時光的方法就是“盯著地毯數螞蟻”。由于無法工作,這些女人生活貧困,完全依賴于運營這些建筑的伊斯蘭慈善機構。日落之后,這里會嚴格實行宵禁,而且針對女性住戶的規定禁止她們穿高跟鞋、修眉毛,甚至嚼口香糖。圖為M,15歲,她最近開始穿戴面紗。她17歲的姐姐剛剛結婚,離開了“烈士遺孀”樓,把她丟給母親和四個兄弟姐妹。她打算讀完高中,并成為教師。
今年9月,作為她拍攝對象的一名少女同意嫁給一個富裕的沙特阿拉伯人當二老婆——她曾發誓要為愛結婚。她告訴哈布朱卡,自己“沒有其他選擇,恐怕只能在公寓里慢慢死去”。圖M和她年少的妹妹S(左)。她們的父親在內戰中戰死。她們的媽媽帶著六個孩子,忽然就有了很大壓力急著要把兩個年長的女兒嫁出去。攝于2012年。
衛星新聞描述了一名戰士在敘利亞內戰中戰死。對于在約旦逃難的敘利亞難民,這樣的畫面在電視機和手機中無處不在。攝于2013年。
H展示手機里她丈夫的照片。她丈夫在自由敘利亞軍服役。她在馬上要生孩子的時候,通過手機短信接到他死亡的消息。她在他去世前幾周時接到這張照片。現在她住在約旦拉姆薩的“烈士遺孀”樓。攝于2012年。
S最小的孩子在午飯前躺在桌布上。H還太小,不能去上學,所以大部分時間只能呆在屋內。盡管物資匱乏,用著基本的食材S還是能用創造性的辦法為孩子們準備好三餐。攝于2014年。
F的弟妹拜訪她家,訴說她的丈夫戰死后自己一路逃亡的恐懼。她和兩個孩子一路從敘利亞的德拉逃到伊拉克,最后回到約旦。攝于2013年。
F,35歲,丈夫死后,她與五個孩子逃離德拉,乘坐的標致汽車上擠得水泄不通。走的時候她給自己的家拍了錄像,以免再也回不去。她帶走了這個木質托盤,因為這是丈夫在去貝魯特的時候買給她的。Tanya給這個系列起名《明天會有杏子吃》(TomorrowThere Will Be Apricots)。這是一則阿拉伯諺語。她說,這句話并不像它聽起來那樣充滿希望。“要沉重多了,”她說。“它隱含的意思是,明天永遠不會到來。”
丈夫生前會從前線給F發一些撩人的短信、詩歌和戰士照片。她通過短信得知丈夫在敘利亞戰場上陣亡。舊手機壞了之后,她就失去了可供回憶的東西。這是她手中唯一一張丈夫在生前發給她的照片。
一對姐妹在“烈士遺孀”樓的客廳里擺姿勢拍照。她們年紀還小,可以上學,而且還可以外出。等她們再大一些,很可能每天就要在公寓里待著,還有可能被迫早婚。
25歲的N與17名流離失所的家庭成員住在一間有兩個臥室的公寓里。上面掛著婆婆的內衣,這是婆婆從敘利亞偷偷帶來的寥寥幾件貼身物品之一。婆婆表示,如果兒子從前線回來,她愿意讓N共用這件睡衣。